|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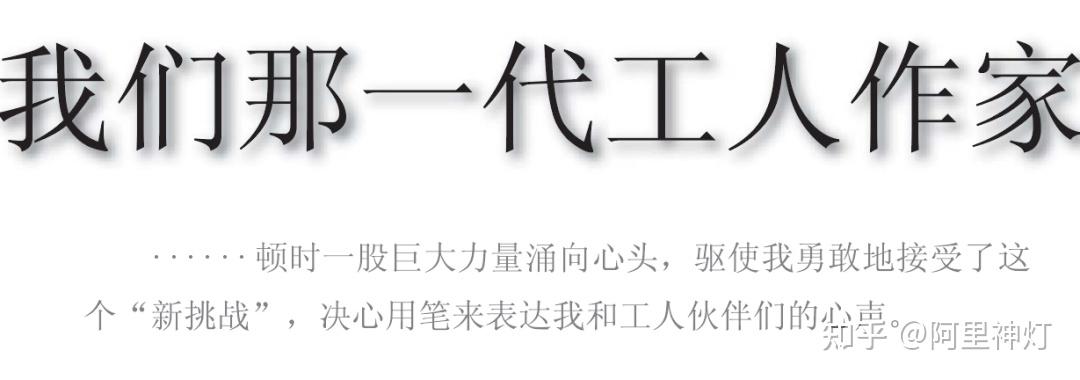
从我个人感受说起。
我原是上海柴油机厂一名技术工人, 解放前只读过三年书, 为了谋生就去当学徒了。1952年因积极参加职工夜校学文化并取得一点成绩, 被评为上海五金工会系统的学习模范, 夜校老师要我写篇获奖后感想, 发表在厂部食堂门口大黑板报上。未料想, 我写的这篇以解放前后学文化的苦与甜为内容的短文, 竟引起当时在厂里参加民主改革的《劳动报》记者唐铁海、杨振龙等人的关注, 他们和厂工会等有关领导研究后找到了我, 说我那篇短文写得有真情实感, 有点写作潜力, 因此鼓励和动员我这个当时已带有几名徒弟的青年老师傅, 担任报社通讯员, 给报刊写稿。我开始不敢答应, 担心自己完不成这像是飞来的陌生任务, 但当我想到每天发生在我周围的各种新鲜的人和事, 想到和我朝夕相处的工人伙伴的各种喜怒哀乐, 顿时一股巨大力量涌向心头, 驱使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新挑战”, 决心用笔来表达我和工人伙伴们的心声。使我很难相信的是, 当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为报刊写新闻报道和小通讯之类稿件时, 总觉得有那么多写不完的事和讲不完的话, 尽管一开始曾遭到十二次退稿的挫折, 但在一些报刊编辑、工人群众的帮助支持下, 我写的稿子终于在报上刊出, 而且是越登越多,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 上海各报刊登我的大小稿件近三百篇。更没有想到的是, 此举会改变我的人生, 使我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漫长之路。
其实, 之所以能在我身上发生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 是和当时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以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解放之初, 党就创办了以发表工农兵作者作品和培养工农兵作者为主要任务的《群众文艺》, 并指示上海各报刊的文艺部门, 大力在厂矿企业中发展工人通讯员, 担负起辅导和培养工人作者的光荣任务。《解放日报》、《劳动报》和上海人民电台为此曾多次举办过通讯员讲习班, 尔后又和市文联等单位合办了工人文艺创作组, 柯蓝、赵自、唐铁海、阿章以及电台编辑王友枚、陈榭等人作为创作组老师和辅导员, 都曾满腔热情地为发现和扶植工人作者, 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劳动。

1956年5月, 作协上海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 几位作家与工人作者在一起。郑成义 (左一) 福庚 (左三) 刘知侠 (左五) 徐锦珊 (左六) 金云 (右四) 靳以 (右三) 陈登科 (右二) 费礼文 (右一)
上海工人文艺创作组吸收了几十名当时算是有点“冒尖”的工人作者, 分别在电台和《劳动报》两处活动, 参加电台这组的学员有唐克新、胡万春等人, 参加《劳动报》这组的学员有毛炳甫、郑成义等人。我是被吸收到《劳动报》这一组的, 但刚开始因我还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 只是参加旁听, 后来才转为正式组员的。我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老兄弟俩》, 就是在我当“旁听生”时写的。稿子是投寄给当时华东作协 (后改为上海作协) 办的文学刊物《文艺月报》, 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跨进巨鹿路作协所在地大门, 见到当时编辑部负责人之一的老作家魏金枝和小说组编辑、女作家罗洪、欧阳翠, 经过他们热情帮助, 这篇习作很快就在《文艺月报》1953年五月号上发表了。从那以后, 我发表在这本刊物上的很多作品, 如小说《早春》、《雨露车辙》、《不落的太阳》等等, 都曾经过魏金枝亲自审阅和指点。这位为人正直的老作家, 为培养文学新人和一批工人作者, 呕心沥血, 作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党的支持和关怀, 许多作家、编辑园丁般地培养和帮助, 再加上自身刻苦努力, 上海一批工人作者开始成长起来。从五十年代初到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召开前, 已产生一些较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如唐克新的《车间的春天》、《古小菊和她的姐妹》, 胡万春的《骨肉》、《青春》, 以及我写的《一年》、《两个技术员》等等,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为此在1954年和1955年, 先后编选出版了《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选集》一、二集, 收有二十名工人作者写的近五十篇作品。与此同时, 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选有很多上海工人作者作品的《工人文艺创作选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第一本短篇集《成长》。中国作协和作协上海分会批准唐克新和我入会, 胡万春等也加入了作协上海分会。
1956年3月, 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 上海代表团中有我和唐克新、胡万春、毛炳甫、福庚、郑成义、徐锦珊、金云八名工人作者。这次会议对推动文学创作特别是青年和工人创作起了积极作用。会后, 作协上海分会和上海团市委建立了专门组织, 加强对青年和工人文学创作小组的领导和辅导, 创办了以发表工农兵和青年作者作品为主的刊物《萌芽》。因而, 从那以后直至六十年代初, 上海工人创作像是进入“黄金期”, 有了很大进展, 写出了不少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其中, 进步较大的是胡万春, 他被推荐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之后, 接连写出《内部问题》、《特殊性格的人》等多篇作品, 出版了《谁是奇迹的创造者》、《红光普照大地》等小说集;唐克新写了《沙桂英》等新作, 出版了《种子》短篇集;海员陆俊超写出《九级风暴》、《幸福的港湾》等作品;我也写了《晨》、《不落的太阳》等中短篇, 出版了第三本小说集《早春》。与此同时, 胡万春和我还积极参与电影和话剧创作, 胡万春创作了电影剧本《钢铁世家》和《家庭问题》, 我则创作了《钢人铁马》、《他们在成长》等五部电影剧本 (其中两部是和艾明之、强明合作的) ;胡万春先和佐临等人合作编写了话剧《激流勇进》, 后又和我及陈恭敏等人编写了话剧《一家人》, 这两个剧本都曾获得中央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创作奖。

1 9 5 6 年3月, 参加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上海八名工人作家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左起:金云、徐锦珊、郑成义、福庚、费礼文、毛炳甫、胡万春、唐克新
围绕上海工人创作的发展, 当时有许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进行过分析和评述, 他们既热情肯定其中一些可取之处, 也中肯指出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如罗荪写的《上海十年工人创作的光辉成就》, 魏金枝写的《上海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巨大收获》 (刊于1959年10月《文艺月报》改名《上海文学》创刊号上) ;又如针对我写的一些作品, 欧阳文彬写了《费礼文的“钢人铁马”》 (《文艺月报》1958年12月号) 、《致费礼文同志》 (《解放日报》1962年11月13日) , 晓立 (李子云) 写了《费礼文短篇创作的新收获》 (《工人日报》1963年2月3日) 等等, 他们从点到面地剖析了当时工人创作的得与失。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 有曲折, 有错误, 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时至今日, 回顾“文革”前十多年上海工人文艺创作这段历史, 从它的基本方面来看, 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 工人文艺创作总是坚持从生活出发, 一些工人作者大都长期生活在工矿企业里, 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和生活在一起的职工、干部同呼吸共命运。拿胡万春、唐克新和我来说, 即使后来成为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 也一直长期生活在各自工厂里。当然,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要创作作品, 不但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 还要认识生活、分析生活, 善于捕捉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东西;不但要联系群众, 还要善于理解人物, 由表及里地洞察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然后按照生活本身发展规律, 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法把它反映出来。在众多工人创作的作品中, 还是有一些能为读者认可的作品, 它们生活气息较浓, 字里行间充满激情, 使人读后能感受到一种生气勃勃、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发人深思的地方。这就在于写这些作品的作者, 是从生活出发, 把在火热斗争生活中感受到的真实东西, 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其次, 工人创作的作品在反映工人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方面, 还是做出一些成绩的。上海作为曾拥有百万产业大军的城市, 如何把他们的劳动生活准确生动地反映出来, 许多作家都曾为此作过努力, 如夏衍曾写过反映纺织工人苦难生活的《包身工》;茅盾的《子夜》,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也都有不少篇幅是反映工人生活的。作为从产业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工人作者, 当然更是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因此, 回顾那段历史, 毕竟还是有一些过去很少见到的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问世, 使得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画廊中或多或少增添了粗手粗脚普通工人和劳动者的人物形象。
当然, 这段历史中的上海工人创作也是“有曲折, 有错误”。这是因为一些工人作者受到“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 不按艺术规律办事, 从概念出发, 把文学作品变成某项政策图解;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写成只见机器不见人的繁琐生产过程, 造成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等等。回顾反省我在这段时期的创作, 更是有着不少深刻教训。例如, 我在创作电影剧本《激流》时, 由于思想上受到“左”的思潮影响, 没有正确理解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不是按照艺术规律, 而是按“中心任务”和“政策要求”去创作。当时, 正是庐山会议后所谓“反右倾”时期, 为了完成这一“主题”, 就根据事先画好的框框, 到生活中去搜集素材, 尔后根据“政策”要求来编故事、安排人物。因此, 尽管当时我在现实生活中, 看到不少因“反右倾”造成的种种恶果, 以及许多浮夸、虚假的东西, 但是我却怕违反“政策”而把它当作“非主流”、“非本质”丢在一旁。不仅如此, 在我后来的创作中, 非但没有揭露因“反右倾”造成危害的种种真实事例, 反而去歌颂一些不讲科学、弄虚作假的错误东西。结果是, 剧本写得似乎离“政策要求”越来越近, 而它所反映的却是离真实生活越来越远。尽管这个剧本后来还是拍成电影发行了, 但是这种只是为了图解某项“政策”和“中心任务”的作品, 又怎么能打动观众的心?只能是过眼黄花而已。
其次, 在我创作的一些作品中, 经过前辈作家、编辑的指点帮助, 虽然也塑造出一些还能为读者接受的老工人、青年工人等人物形象, 但更多的人物形象却显得肤浅和苍白无力。其教训就在于我脑子里曾有个“框框”, 塑造工人形象时总怕给他们脸上抹“黑”, 把人物给歪曲了, 例如我在写一篇反映工人搞技术革新小说时, 开始写得还较为生动, 既写了主人公的欢乐, 也写了他的痛苦;既赞扬了他的顽强意志, 也鞭挞了他的内在缺点和丑陋东西。但等到我按“政策”框框去衡量它时, 又开始害怕起来, 感到这儿不符合先进典型标准, 那儿有损人物形象, 于是先对它一遍一遍地“磨平”, 把原先尚能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些生动情节, 都当作“犯忌”东西“磨”掉, 使原本还有点独特个性的人, “磨”得几乎没有什么凹凸面了。然后, 再脱离生活实际地对人物进行“拔高”, 向所谓“高大英雄形象”靠拢, 不断加大他的“英雄行为”和“豪言壮语”, 直至顾不得吃顾不得睡, 没有家庭生活, 更不许谈情说爱等等, 经过如此“磨平”与“拔高”, 这样的人物还能真实可信生动感人吗?其结果只能成为图解某项“中心任务”的干巴巴的“木偶”而已。
回顾“文革”前工人创作这段往事, 反思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创作经历, 感触甚深, 心情也是沉重的。但历史毕竟是历史, 它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上海工人创作的真实写照, 你想抹也是很难抹掉的, 还不如完整地把这些经验教训提供出来, 给关心和愿为反映广大工人群众和劳动者生活的创作者、研究者作参考资料吧!
来源:《档案春秋》2007年04期,作者费礼文 |
|